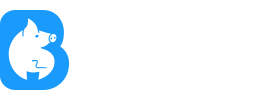大家好,感谢邀请,今天来为大家分享一下石家庄到西安多少公里的问题,以及和石家庄到西安多少公里路程高速, 石家庄到西安多少公里的一些困惑,大家要是还不太明白的话,也没有关系,因为接下来将为大家分享,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,解决大家的问题,接下来就开始吧!
一九九三年的秋天,天总是很高,蓝得像一块假布。我开着那辆解放牌大卡车,在光秃秃的国道上跑,感觉自己就是个铁壳子里的小甲虫,没完没了地往前爬。
车是我吃饭的家伙,也是我的家。驾驶室里,除了方向盘和仪表盘,剩下的地方都塞满了我的家当。副驾驶座上扔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军大衣,是我当年从部队带回来的,后背上磨出了一个洞,一直懒得补。车厢里永远飘着一股味儿,柴油味混着劣质烟草的焦糊味,闻久了,也就成了我自个儿的味儿。
老婆走了快三年了,家里没人等,我也就懒得回。拉完一趟货,就在车里睡,或者在路边的小旅馆对付一宿。日子像卡车轱辘,一圈一圈,单调,麻木。
那天下午,我从山西拉了一车煤往河北送,路过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土坡。坡上站着个姑娘,孤零零的,身边一个行李都没有,风吹着她那身单薄的蓝布褂子,像要被吹跑的纸人。
跑大车的,有不成文的规矩,尽量不拉人,尤其是女人。麻烦。可那天鬼使神差,我看着她在秋风里缩着脖子的样子,心里那块硬邦邦的地方,像是被针扎了一下。我踩了刹车,铁家伙发出一声刺耳的长鸣,停在了她跟前。
“上来吧。”我没多话,朝副驾驶那边努了努嘴。
她拉开车门,手脚并用地爬了上来,关上门,把外面的风和尘土都隔绝了。一股冷气也跟着带了进来。她缩在副驾驶座上,离我远远的,双手抱着膝盖,一句话也不说。
我从后视镜里瞟了她一眼,二十岁上下的样子,脸很干净,就是有点蜡黄,像是饿了很久。嘴唇干得起了皮。
我没问她从哪来,为什么一个人在这。出门在外,谁没点难处。问多了,像是在揭人伤疤。
车子重新发动,发动机“突突突”地响着,像是头老牛在喘气。我们俩一路无话,只有发动机的声音和轮胎碾过路面的沙沙声。天色一点点暗下来,车灯在漆黑的国道上划开两道昏黄的光。
到了石门地界,已经是晚上九点多。我在一个还亮着灯的大车店门口停下。我对她说:“到了,下车吧。”
她像是刚从梦里惊醒,茫然地看了看窗外,又看了看我。车外的灯光照在她脸上,我看见她眼睛里全是慌乱。
“大哥……”她开口了,声音细得像蚊子叫,“我……我没地方去。”
“我……我来找人,可……可那人找不到了。”她的声音里带了哭腔。
我心里咯噔一下,最怕的麻烦还是来了。我皱着眉头,点了根烟,猛吸了一口,烟雾缭绕里,我看着她那张快要哭出来的脸。那年头,骗子多,什么仙人跳、合伙偷东西的,听得多了,不能不防。
她低下头,抠着自己的手指甲,半天不说话。车厢里安静得可怕。我听见她吸鼻子的声音,一下,又一下,压抑着,不敢哭出声。
我心里的那点硬气,就这么被她一下一下地吸没了。我烦躁地把烟头摁灭在烟灰缸里,说:“行了行了,别哭了。这么晚了,一个姑娘家,你能去哪。”
她抬起头,眼睛红红地看着我,像是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。
“大哥,我……我能不能……”她咬着嘴唇,半天说不出来。
她猛地点头,眼泪差点掉下来。
我长长地叹了口气。跑了这么多年车,头一回遇上这种事。我看了看她单薄的身子,又看了看窗外黑漆漆的夜。把她一个姑娘就这么扔在路边,万一出点什么事,我这辈子心里都过不去。
“睡后面吧。”我说。
驾驶室后面有一张窄窄的卧铺,平时我累了就在那躺会儿。卧铺上堆着些杂物和我的被子。
“谢谢大哥!谢谢大哥!”她连声说着,像是怕我反悔。
“别谢了,早点睡。”我把卧-铺上的东西收拾了一下,把我的被子抖开。一股子烟味和汗味。她好像没闻见,或者不在乎。
我把副驾驶座上的那件旧军大衣拿过来,扔给她:“晚上冷,盖着点。”
她抱着那件军大衣,愣愣地看着我。
我没再看她,拉上了驾驶室和卧铺之间的布帘子,重新点了根烟,靠在驾驶座上,看着窗外发呆。
那晚,我没去旅店,就坐在驾驶座上。布帘子后面,是她均匀的呼吸声。我听着那呼吸声,一夜没睡踏实。心里乱糟糟的,像一团被猫抓过的毛线。
我,姜卫国,一个三十五岁的单身汉,在我的铁皮屋子里,收留了一个来路不明的姑娘。我不知道,这究竟是捡了个麻烦,还是别的什么。
02 一碗面的温度
天蒙蒙亮的时候,我被冻醒了。秋天的清晨,寒气像针一样往骨头里钻。我动了动僵硬的脖子,扭头看了一眼后面的布帘子,里面一点动静都没有。
我轻手轻脚地下了车。露水很重,车窗上蒙了一层白雾。我绕着车走了两圈,抽了两根烟,脑子才算清醒过来。
天亮了,她该走了吧。我想。萍水相逢,一晚上的安稳,也算是仁至义尽了。
见我上来,她吓了一跳,赶紧把碗藏到身后,像个偷吃东西被抓到的小孩。
“你……你醒了,姜大哥。”她小声说。她大概是听过店老板这么叫我。
我的目光落到她藏在身后的碗上。是两个馒头,掰碎了泡在热水里。我的暖水瓶就放在她旁边,里面的水已经下去了一半。
我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拧了一下,有点疼。
她低下头,“嗯”了一声。
“跟我下车。”我把驾驶座上乱七八糟的地图、票据往旁边一扒拉,语气还是硬邦邦的。
她不知道我要干嘛,有点害怕,但还是顺从地跟着我下了车。
一碗牛肉面
大车店旁边有个小饭馆,门上挂着块油腻腻的布帘子,上面写着“兰州拉面”。我掀开帘子走进去,回头对她说:“进来。”
店里只有两三桌客人,都是和我一样的司机,正埋头“吸溜吸溜”地吃面。我找了个干净点的位置坐下,对她说:“坐。”
她拘谨地在对面的长凳上坐下,只坐了半个屁股。
“老板,两碗牛肉面!大碗的!多加肉!”我冲着后厨喊。
她猛地抬头看我,摆着手说:“不不不,姜大哥,我吃馒头了,我不饿……”
“让你吃就吃,哪那么多废话。”我瞪了她一眼。
她不敢再说话了,低下头,两只手放在膝盖上,一动不动。
面很快就上来了。两大碗,热气腾腾,上面飘着红亮的辣油和翠绿的葱花,大片的牛肉铺了满满一层。那股香气,让饿了一晚上肚子的我也忍不住咽了口口水。
“吃吧。”我把筷子递给她。
她拿起筷子,却没有动,只是看着那碗面。我看见她的眼圈又红了。
“趁热吃,凉了就不好吃了。”我自顾自地挑起一筷子面,大口吃起来。
她大概是看我吃了,才终于低下头,也学着我的样子,挑起一小撮面条,慢慢地放进嘴里。她的动作越来越快,像是饿了很久的猫,终于见到了鱼。她吃得很快,但很安静,没有发出一点声音。一碗面很快就见了底,连汤都喝得干干净净。
吃完了,她抬起头,脸上有了点血色,嘴唇也红润了。她看着我,小声说:“姜大哥,谢谢你。我叫林晓萍。”
“姜卫国。”我说。
回去的路上,她的话多了起来。也许是一碗热汤面暖了她的胃,也暖了她的心。
她断断续续地讲了她的事。她家在南方一个很远的小县城,家里穷,弟妹多。前阵子,村里来了个“城里人”,说是石家庄这边的工厂招工,包吃包住,工资还高。她动了心,瞒着家里,凑了点路费,就跟着那人来了。结果到了这,那人把她身上最后一点钱骗光,就不见了。她找了好几天,人才市场、小巷子,都找遍了,也没找到。她不敢回家,也没脸回家。
“我就是个傻子。”她低着头,声音里满是懊悔。
我没说话,只是默默地开着车。这种事,那年头太多了。多少怀着梦想的年轻人,就这么被骗得一无所有。
“我有个远房姨妈,嫁到了陕西那边。我想……我想去投靠她。”她说,“就是……有点远。”
我沉默了。石家庄到陕西,一千多公里。我这趟货只到这里。
车里的气氛又沉闷下来。她大概也知道这事不现实,说完就没再开口。
我把车开到货场,卸了煤,拿了运费。走出结账的办公室,看见林晓萍还乖乖地坐在副驾驶上,透过车窗看着我,眼神像只被抛弃的小狗。
我站在车下,抽了半根烟。货场里人多眼杂,我能感觉到已经有好几道目光在我们车上打转了。我心里烦躁。
我拉开车门,上了车,从兜里掏出一百块钱,递给她:“拿着,自己买张火车票去陕西吧。”
一百块,是我这趟活小半的利润了。
林晓萍看着那张钱,却使劲摇头:“不,姜大哥,我不能要你的钱。你让我搭车,还请我吃饭,我已经……我已经很过意不去了。”
“拿着!一个姑娘家,身上没钱怎么行!”我把钱硬塞到她手里。
她捏着那张钱,眼泪“啪嗒”一下就掉了下来。她没说谢,我也没说不用。有些事,说开了,就跟那刚冒热气的馒头见了风,一下就凉了,硬了。
她哭了半天,才抬起头,看着我说:“姜大哥,我……我给你打个欠条吧。等我找到我姨妈,挣了钱,我一定还你。”
“行了。”我摆摆手,发动了车。
我本想把她送到火车站就走。可车开到一半,我又改了主意。
“我下一趟活,正好要去趟西安。你要是信得过我,就再坐几天我的车吧。”话说出口,我自己都吓了一跳。
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么说。也许是看她太可怜,一个姑娘家,我不放心。也许是……也许是那碗牛肉面,她吃得那么香的样子,让我这个光棍汉,心里某个地方,塌陷了一块。
林晓萍愣住了,好半天才反应过来,她看着我,眼睛里亮晶晶的,像是装了天上的星星。
“姜大哥,你……你是个好人。”
那一天,我开着空车,载着林晓萍,重新上了国道。目的地,陕西。我跟自己说,就当是积德行善了。可我心里明白,有什么东西,已经不一样了。
03 车厢里的皂角香
一个“家”的雏形
自从决定带林晓萍去陕西,我那辆解放大卡车的驾驶室,就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
以前,这儿就是个狗窝。脏衣服、臭袜子、吃剩的饼干袋子,随手乱扔。可林晓萍来了之后,一切都变了。
她似乎很过意不去白坐我的车,总想找点活干。第一天,她趁我去找货源的时候,把整个驾驶室都擦了一遍。仪表盘擦得锃亮,玻璃擦得能照出人影。那些我塞在角落里积了灰的票据,她都给我理得整整齐齐,用一根不知道从哪找来的绳子捆好。
我回来的时候,一拉开车门,差点以为上错了车。
“你弄这个干啥,乱七八糟的,我习惯了。”我嘴上这么说,心里却熨帖得很。
她只是对我笑笑,没说话。
第二天,她不知道从哪弄来一小块肥皂,把我攒了一星期的脏衣服全给洗了。她就在路边的小河沟里,蹲着身子,一下一下地搓。秋天的河水已经很凉了,我看见她手冻得通红。
“行了,别洗了,回头找个旅店用洗衣机。”我看不下去了。
“没事的,姜大哥,马上就好。”她头也不抬。
衣服晾在驾驶室外面拉的绳子上,像一面面小旗子,迎风飘扬。晚上收进来,带着一股淡淡的、干净的皂角香味。那股香味,很快就盖过了车里常年不散的柴油味和烟味。
我躺在卧铺上,闻着那股皂角香,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。好像这个铁皮壳子,不再只是一个移动的工具,开始有了一点……家的味道。
我很快就联系好了一趟从石门拉棉花去西安的活。装好车,我们正式上路。
路途漫长,我们的话也渐渐多了起来。她会给我讲她小时候在村里掏鸟窝、摸小鱼的事。我呢,就跟她吹牛,讲我当兵时候的趣事。大多数时候,是我说,她听,睁着一双亮晶晶的眼睛,像是在听什么了不得的传奇故事。
有一天晚上,我们在服务区过夜。天冷,我把那件旧军大衣又拿了出来。车里的灯很暗,她看见了我后背上那个磨出来的破洞。
“姜大哥,你这衣服破了。”她说。
“破了就破了,还能穿。”我满不在乎。
“我……我帮你补补吧。”她小声说。
她点点头,“我娘教我的。我弟妹的衣服,都是我补的。”
说着,她不知道从哪掏出一个小小的针线包,里面几卷彩色的线,几根长短不一的针,收拾得井井有条。
她让我把军大衣脱下来。就着昏黄的车内灯,她开始一针一线地缝补起来。她的手指很巧,穿针引线的动作熟练又好看。我坐在旁边,抽着烟,看着她。
灯光下,她的侧脸很柔和,长长的睫毛在眼睑下投下一小片阴影。她那么专注,仿佛手里捧着的不是一件破衣服,而是一件稀世珍宝。
我看着看着,就有些恍惚。我想起了我那过世的媳妇。她也有一双这么巧的手。以前,我的衣服破了,她也是这样,在灯下,一针一线地给我补。
她的手顿了一下,没有抬头,轻轻“嗯”了一声。
“我娘……也总是在晚上给我补衣服。”她的声音很低,带着一丝沙哑。
车厢里又安静下来。只有她手里针线穿过布料的“沙沙”声。那一刻,我觉得我和她之间,好像有了一种不用言语的默契。我们都是离家在外的人,心里都装着一个回不去或者不敢回的家。
那个洞,她补了很久。她没有用简单的针法随便缝上,而是找了一块颜色相近的布头,仔仔细
细地缝了一个很平整的补丁。针脚细密得几乎看不出来。
她把补好的军大衣递给我,像是完成了一件大事,脸上带着一点小小的得意。
“姜大哥,你试试。”
我把军大衣穿上,后背那个曾经漏风的洞,现在被一块温暖的布料贴着,暖洋洋的。那暖意,好像顺着脊背,一直传到了心里。
“手艺不错。”我故作平静地说。
她笑了,笑得很好看,像一朵在夜里悄悄开放的小花。
从那以后,那件军大衣我就不舍得随便乱扔了。每次脱下来,都叠得整整齐齐放在卧铺上。那块小小的补丁,像是一个烙印,烙在了衣服上,也烙在了我心里。
那年头,跑大车的,车就是家。可我那晚才明白,铁皮壳子装的只是身子,能装下心的,得是个人。
林晓萍的出现,就像往我这个空了很久的铁皮壳子里,塞进了一团温暖的棉花。
04 服务区的风言风语
王胖子的玩笑
路过河南境内一个大服务区的时候,我碰到了王胖子。
王胖子也是跑长途的,跟我认识好几年了。人是个热心肠,就是嘴碎,说话不过脑子。
“拉趟棉花去西安。”我笑着捶了他一拳。
我的脸“刷”地一下就红了,心里一阵烦躁。
服务区人多嘴杂,司机们聚在一起,最爱聊的就是这些荤素不忌的闲话。林晓萍在车上,这事早晚得传开。
“别瞎说!人家是搭车的,一个小姑娘,遇上难处了,我顺路捎一段。”我压低声音解释。
我懒得跟他解释,打完水就往回走。一路上,我觉得背后有好几双眼睛盯着我,那些目光像针一样,扎得我浑身不自在。
“没事。”我把暖水瓶重重地往地上一放,溅出几滴热水。
她吓了一跳,不敢再问了。
那天下午,我的火气就没下去过。
我姜卫国,退伍兵出身,跑车这么多年,靠的是本分和力气。我最在乎的就是个名声。现在倒好,平白无故地,就成了别人嘴里的桃色新闻。
我越想越憋屈。这憋屈,有一半是冲着那些碎嘴的同行,另一半,却不知道为什么,是冲着林晓萍。
我觉得是她的出现,打破了我平静的生活。如果没有她,我还是那个独来独往的姜卫国,没人会议论我,没人会拿我开涮。
车子开出服务区,我一路上一言不发,车开得又快又猛。
林晓萍似乎感觉到了我的情绪,安安静静地坐在旁边,大气都不敢出。
开到一个岔路口,我一脚急刹车。她没坐稳,头一下子撞在了前面的挡风玻璃上,“咚”的一声。
“对不起……”她捂着额头,小声道歉。
那句“对不起”像一根导火索,瞬间点燃了我心里的那股邪火。
“对不起有什么用!”我冲她吼道,“你知不知道因为你,别人在背后怎么说我!说我拐带小姑娘,说我金屋藏娇!我姜卫国的脸都让你给丢尽了!”
我吼完,自己也愣住了。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说出这么重的话。
林晓萍也愣住了,她捂着额头,难以置信地看着我。她的眼睛里先是惊讶,然后是委屈,那点光亮一点点地暗了下去。
她没哭,也没反驳,只是慢慢地把手从额头上放下来,低着头,轻声说:“姜大哥,对不起,我……我是个麻烦。”
她的声音很平静,平静得让我心慌。
“我……我不是那个意思……”我想解释,却又不知道该从何说起。
“我知道。”她说,“前面要是有车站,你放我下来吧。我自己走。”
我重新发动了车,但车速慢了很多。我没说话,她也没说话。那股淡淡的皂角香,似乎也被这尴尬的气氛冲淡了,车里又只剩下沉闷的柴油味。
我第一次意识到,让一个女人进入我的生活,不仅仅是多一双碗筷,多一个人说话那么简单。它还意味着责任,意味着要面对外界的眼光和压力。而我,好像还没准备好。
我的那层硬壳,在别人的风言风语面前,又悄悄地合上了。我伤害了她,也困住了自己。
05 雨夜里的那件军大衣
和林晓萍吵完架,车里的气氛就降到了冰点。她不再说话,也不再忙活,只是安静地缩在副驾驶座上,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风景。那风景荒凉,就像我当时的心情。
我好几次想开口道歉,但话到嘴边,又咽了回去。男人那点可怜的自尊心,像块石头堵在喉咙里。
天色渐渐暗了,还下起了雨。先是淅淅沥沥的小雨,很快就变成了瓢泼大雨。雨刮器开到最大,在挡风玻璃上疯狂地摆动,也只能划开一道模糊的视野。
车子开进秦岭山区,盘山公路又窄又滑。我打起十二万分的精神,握着方向盘的手心里全是汗。
就在一个陡坡上,车子突然“吭哧”了两声,发动机的声音变得不对劲,然后猛地一震,彻底熄火了。
我心里一沉,坏了。
我试着重新打火,可除了“咔咔”的空响,一点反应都没有。车子就这么死在了半山腰上,前不着村,后不着店。雨点“噼里啪啦”地砸在车顶上,像是要把它砸穿。
“没事,小问题。”我嘴上安慰她,心里却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。这种鬼天气,这种鬼地方,车坏了,简直是要命。
我披上雨衣,拿着工具箱下了车。冰冷的雨水瞬间浇了我个透心凉。我打开引擎盖,一股热气冒了出来。我打着手电筒,借着微弱的光检查。是发动机的管子出了问题。
我趴在冰冷泥泞的地上,钻到车肚子底下,开始修理。雨水顺着我的脖子往衣服里灌,冷得我直打哆嗦。扳手在湿滑的螺丝上一次次打滑,我越急,手越不听使唤。
不知道过了多久,我终于把管子接上了。我从车底爬出来,浑身已经没有一处是干的,脸上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汗水。
回到驾驶室,我像个落汤鸡。林晓萍递过来一块干毛巾。我胡乱擦了擦脸,重新打火。
发动机“突突”了两声,终于又欢快地唱了起来。
我长舒了一口气,整个人都快虚脱了。
车子重新上路,可我却感觉越来越不对劲。头晕得厉害,眼皮发沉,身上一阵冷一阵热。我知道,我这是淋了雨,发烧了。
我强撑着又开了一段路,但手脚越来越不听使唤,方向盘都快握不住了。在一个稍微平坦点的路肩,我把车停下。
“不行了……我得歇会儿。”我趴在方向盘上,感觉骨头缝里都在冒寒气。
“你发烧了!”她惊叫起来。
我“嗯”了一声,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。
后面的事,我就有些迷迷糊糊了。我感觉林晓萍把我扶到了后面的卧铺上,给我盖上了被子。她在我车里翻箱倒柜,像是在找什么。
“……工具箱里,有个小铁盒。”我含糊地说。
我听见她下车的声音,雨声,开工具箱的声音,然后又回到车上。她把几片药塞进我嘴里,又端着水杯,一点一点地喂我喝下去。水很烫,暖流顺着喉咙一直流到胃里,我稍微舒服了一点。
我烧得越来越厉害,开始说胡话。一会儿喊着我妈,一会儿又喊着我那过世的媳妇。我感觉自己掉进了一个冰窟窿,怎么也爬不出来。
迷糊中,我感觉到一双冰凉的手在给我擦脸,擦脖子。是一条湿毛巾。林晓萍一遍又一遍地用冷水给我物理降温。
“水……水……”我渴得嗓子冒烟。
她又一次把水杯凑到我嘴边。
深夜里,我被一阵寒意冻醒。我睁开眼,发现盖在我身上的被子滑掉了。我挣扎着想去拉,却浑身无力。
就在这时,一件厚实、温暖的东西盖在了我身上。那东西很重,带着一股熟悉的、淡淡的皂角香。
我费力地转过头,借着窗外偶尔闪过的车灯光,我看见林晓萍正坐在卧铺边上,打着瞌睡。她把我的那件旧军大衣,盖在了我的身上。
我伸手摸了摸胸口,摸到了那件军大衣。我又摸了摸后背,摸到了那个平整、细密的补丁。
那补丁,正贴着我的后心,暖烘烘的。
那一刻,雨声、风声、发动机的余温,好像都消失了。我的世界里,只剩下那件军大衣的重量和那块补丁的温度。
我看着林晓萍瘦弱的背影,她就那么坐着,守着我,像一尊小小的、坚韧的雕像。这个被我吼过、被我当成“麻烦”的姑娘,在我最狼狈、最无助的时候,却成了我唯一的依靠。
我那颗用坚硬外壳包裹了三年的心,在那个风雨交加的夜晚,被一件补过的军大衣,和一个瘦弱姑娘的守护,彻底击碎了。
我闭上眼睛,眼角有温热的液体滑落,混进了冰冷的雨水里。
我心里有个声音在说:姜卫国,就是她了。等到了西安,跟她挑明了,带她回家。别再跑车了,守着她,好好过日子。
06 清晨的告别
雨停了,天也亮了。
我醒来的时候,烧已经退了。身上黏糊糊的,但人清爽了不少。林晓萍趴在卧铺边上睡着了,身上只搭着一件薄薄的外套,长长的睫毛上还挂着晶莹的露珠。
我轻轻地把我的被子拉过来,盖在了她身上。
“好多了。”我看着她布满血丝的眼睛和苍白的脸,心里又酸又软,“辛苦你了。”
她摇摇头,笑了:“你没事就好。”
那一刻,我们之间所有的尴尬和隔阂都烟消云散了。有些东西,不用说,彼此都懂了。
车子重新上路,气氛和之前完全不同。我们话不多,但车厢里流动着一种温暖的默契。我会时不时从后视镜里看她一眼,她会对我笑笑。她把暖水瓶灌满了热水,放在我手边。她把面包撕成小块,递到我嘴边。
我像个大爷一样享受着她的照顾,心里美滋滋的。我开始盘算着未来的日子。等到了西安,送她到她姨妈家,我就跟她姨妈提亲。不,不能空手去。我得先去买点好东西,烟酒、点心,一样不能少。然后我就跟她说,让她跟我回老家。我那房子虽然旧,但收拾收拾也能住。我不跑车了,就在县城找个活干,凭我开车的手艺,饿不死。我们……我们还可以生个孩子……
我一边开车,一边想着这些,嘴角忍不住地上扬。我觉得天从来没有这么蓝过,路边的白杨树也格外挺拔。
林晓萍似乎也感觉到了我的好心情,她哼起了小曲。是首我没听过的南方小调,软软糯糯的,很好听。
我心里那簇叫“希望”的火苗,在那个清晨,烧得正旺。
离她姨妈所在的那个县城,还剩下不到一百公里。天色又晚了。我不想连夜赶路,就在路边一个小镇上找了个小旅馆。
“今晚别在车上睡了,又潮又冷。去旅馆,好好洗个热水澡,睡个安稳觉。”我对她说。
我开了两个房间。这是我们认识以来,第一次分开过夜。
吃晚饭的时候,我要了两个小菜,还破天荒地要了一瓶啤酒。
“晓萍,等把你送到地方,我就……”我喝了口酒,壮着胆子,想把心里的话说出来。
“姜大哥,”她却打断了我,“谢谢你。要不是你,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”
“谢啥。”我摆摆手,“以后……以后有我呢。”后半句,我说得很轻。
她好像没听见,只是低着头,慢慢地吃着饭。
那一晚,我躺在旅馆嘎吱作响的床上,翻来覆去地睡不着。我一遍一遍地在心里演练着明天要说的话。我想象着她听到后又惊又喜的表情。我甚至想好了,如果她答应了,我们回程的路上,要去趟省城,给她买一身新衣服。
想着想着,我抱着被子,傻笑了起来。
第二天,我起了个大早。天还没亮,我就去敲她的房门。
敲了半天,没人应。
我心里一慌,找来老板打开门。房间里空荡荡的,被子叠得整整齐齐,像没睡过一样。
我疯了一样地冲向停车场。我的解放大卡车还静静地停在那儿。我一把拉开车门。
副驾驶座上,空无一人。
座位上,整整齐齐地叠着我的那件旧军大衣。军大衣上面,压着几张叠起来的钞票,还有一封信。
我颤抖着手,拿起那封信。信纸是小学生用的作业本纸,撕下来的。上面的字,写得很娟秀。
“姜大哥:
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,我已经走了。请你原谅我的不告而别。
你是个好人,是我这辈子遇到的最好的人。这几天,是我长这么大,过得最安稳、最踏实的日子。你给我买的牛肉面,是我吃过最好吃的东西。你那辆大卡车,比我自己的家还让我安心。
我能感觉到你的心意。正因为这样,我才必须走。
我这样的一个不清不楚的人,会是你的麻烦,会拖累你的。我听王大哥他们说了,你是个本分人,名声比什么都重要。我不能毁了你。
那一百块钱,我不能要。我身上还有你上次给的钱,足够我坐车了。这几张,是我自己攒的一点,不多,你拿着,就当是我付的饭钱和车费。虽然我知道,你的恩情,我一辈子都还不清。
军大衣我给你补好了,天冷了,你要多穿点。别总抽那么多烟,对嗓子不好。开车别太快,累了就歇歇。
姜大哥,你忘了我吧。就当路上捡了只流浪猫,喂了几天,它自己跑了。
你一定要过得好好的。
信很短,我却看了很久。每一个字,都像一把小锤子,敲在我的心上。
我拿起那几张钞票,有零有整,皱巴巴的,一共是二十七块五毛。这大概是她身上所有的钱了。
我慢慢地拿起那件军大衣,把它紧紧地抱在怀里。上面还残留着她的体温,和那股淡淡的皂角香。可我知道,这股香味,很快就会散尽。车里,将重新被柴油和香烟的味道占满。
我坐在驾驶座上,看着空荡荡的副驾驶,看了很久很久。
天亮了,小镇在晨光中醒来。我发动了车子,发动机“突突突”地响着,还是那么沉闷。
我把车开上国道,继续往前。
路还在前方,一望无际。只是,车里,已经和从前不一样了。也永远,回不到她来之前的样子了。
石家庄到西安多少公里相关信息就介绍到这里,石家庄到西安多少公里路程高速, 石家庄到西安多少公里的问题希望对你有所帮助。